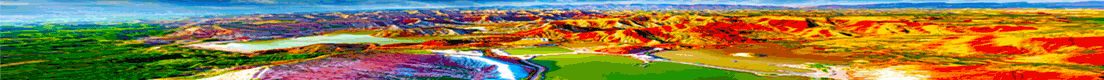她是新中國開國元勛陳賡大將的妻子,她也曾是南京城里的“洋學生”、投奔延安的文工團女戰(zhàn)士、解放區(qū)的民運工作人員、中共中央組織部的干部……她也是大家庭中的女兒、孩子們的母親。聽傅涯的女兒來講述母親,可以看到一代中國人的斑斕歷史。
2010年1月4日,開國大將陳賡的夫人傅涯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享年92歲。49年前,陳賡逝世,留下了自己43歲的妻子和五個孩子。其中傅涯所生的四個孩子中,最小的才5歲,而二女兒陳知進那年不滿11歲。
陳知進對于自己父親母親的故事,是在成年以后很久才慢慢了解得多起來。她越搜集整理父母的事跡資料,就越懷念他們。
從西安到延安:熱血青年之路
我母親原名叫傅慧英。1938年她進入延安的抗大第四期,那年她20歲。她在上中學的時候就參與抗日運動,游行、募捐。有一天募捐的時候募到了一個旅館里,那個地方不太好,用現(xiàn)在的話說就是有色情活動。結(jié)果被我們家一個親戚看見了,就告訴我外公,說她怎么到那些地方去了?我外公就反對她去做這些事。但是后來,他也沒辦法管我媽了,她去了西安。不光是她去,還帶了她一個弟弟一個妹妹,去西安,是為了上延安。
上延安的事,是我大舅給促成的。我大舅這個人,在1925年參加過大革命和北伐,當時在林伯渠領(lǐng)導下的6軍政治部工作,非常進步。大革命失敗后他到了國外,抗戰(zhàn)初期時回國在銀行里工作,后來到西安開了一個酒家。我舅舅與共產(chǎn)黨許多人都非常熟,正好林伯渠領(lǐng)導的八路軍辦事處就在西安,這樣我媽媽去延安就比較順利。后來我媽媽到了延安后還碰到了許多當年在我們家里出入過的共產(chǎn)黨員。
到了延安,我媽媽就改名叫傅涯了。那時去延安的人大多數(shù)都改名。像我舅舅,連姓都改了。為什么?是怕連累留在國統(tǒng)區(qū)的家人。
我今天看我媽媽當年上中學時的照片,覺得可真夠時髦的??赡芎髞淼娜藭?,從一個大城市里的“洋學生”到延安窯洞里吃小米的女戰(zhàn)士,這個生活變化太大了,人是怎么適應過來的?其實我還真沒有聽母親講過當年自己怎么怎么適應不了,對于他們這些滿懷理想的熱血青年來說,艱苦不是問題。我只記得她說過一次:那次是運糧食,走得滿身大汗,累得找個窯洞睡著了,再起來后全身疼得都走不了路。那次得的是風濕性關(guān)節(jié)炎,后來她又犯過。當時幸虧靠她的戰(zhàn)友蘇明阿姨照料才慢慢好起來。
共同的信念使她與陳賡走到一起
傅涯是1940年在八路軍總部所在地山西武鄉(xiāng)縣第一次見到陳賡的,那年,陳賡37歲,他的妻子王根英已經(jīng)犧牲一年。而傅涯是22歲,家里本來有一個未婚夫,是她的表哥。
我媽媽當時在抗大總校文工團有點名氣。因為她有文化,她什么劇都演,話劇,京劇,而目都演主要角色,在那個年代就算個“腕兒”了。后來有人說我爸是看見媽媽演《孔雀東南飛》時看上她的,她堅決否認。其實他倆認識是當時我爸在八路軍總部養(yǎng)病,到他的戰(zhàn)友王智濤家串門。王智濤問他:你現(xiàn)在過得怎樣?我爸說,不錯,現(xiàn)在挺好的,有馬,有槍,有警衛(wèi)員,就是缺個老婆!王智濤當時是抗大總校的訓練部長,而他的愛人吳靜是我媽的同學。于是,他們就把我媽媽叫來,說是借道具啊還是干什么,我媽媽就跟著幾個人去了,第一次見到了我爸爸。
后來,我爸爸就發(fā)動攻勢。只要認識我媽媽的人,我爸爸都去做工作,讓他們?nèi)フf我爸爸怎么怎么好。我媽媽說,她當時反正是如雷貫耳,到處都有人跑來跟她說陳賡這人好。我媽媽最感動的是他毫不忌諱地跟她講自己跟王根英的感情,我媽媽覺得一個人能在感情上這么忠誠,有這么深沉的愛,這個人大概應該是不錯。
我媽媽告訴我爸說,她在老家是有個未婚夫的。我爸就說,你要注意政治啊。結(jié)果我媽寫信給表哥,讓他來延安,他不愿意來。當時我媽對于近親結(jié)婚本來是有顧慮的,因為她看到過我大舅因為近親結(jié)婚,連續(xù)生了兩個啞巴孩子。但是,最終使這樁婚事吹掉的,是因為她的表哥不愿來延安。而我爸媽最終的結(jié)合,還是有共同的革命理想這一點最為關(guān)鍵。
我爸媽是在1943年2月25日結(jié)婚的。劉伯承專門把自己的房子騰出一間給他們住,小房間里正好放張床,外頭就是劉伯承的辦公室。結(jié)婚的時候,我爸對我媽說過三條諾言:“一、我會尊重你的革命事業(yè)心,不會妨礙你對前途進取的努力;二、也不會把你調(diào)到我的身邊做秘書;三、我會愛你到永遠,這是真心。”結(jié)婚后我媽在太岳軍區(qū)司令部大院沒住幾天,就到縣里去搞民運工作了。
我媽是個非常要強的人,當時工作忙起來就不回家,大概一禮拜回來一兩次,后來電視劇《陳賡大將》中描寫,我爸爸想見媽媽了,他就帶著人去喊她回來。他確實是這樣喊過,但是不是像電視劇說的那樣帶著戰(zhàn)士喊的。那是在延安整風那年,他們兩人都回到了延安參加整風。回去后,當時黨校一部都是高級干部,我爸爸就在里面;像我媽媽這一級的就在黨校二部。一部和二部是被延河水隔開的。我媽媽在黨校二部參加好多工作,比如跟著冼星海搞秧歌改革,有時候很忙就回不來。我爸爸想她了,就帶著一幫子人跑到河邊。一般在搗亂時他不會帶戰(zhàn)士的,他帶的是黨校一部的同學,都是像他那種級別的干部。他們到延河邊上喊:“傅涯回來!”這樣喊來喊去就喊出名了,大家都知道我爸爸隔著河喊老婆,我媽就覺得特丟人,回來就會生他的氣。
到了我爸爸上前線打仗的時候,我媽媽會很長時間見不到爸爸。有一次,大概是打洛陽戰(zhàn)役的時候,有人讓我媽去部隊看爸爸,我媽媽帶著我哥哥就去了。好長時間沒見爸爸,哥哥見了爸爸就把他往床底下踢,還說,這叔叔是哪來的?但是我爸一看我媽來了,就說,現(xiàn)在戰(zhàn)爭打得很緊,你要來了,其他家屬也要來,這里工作就不好做了。當時我媽馬上就回去了,很支持我爸的工作。最后是在部隊打過長江后,條件好了,他們才有比較長的時間在一起。
孩子們的母親
在陳知進收集的母親相冊里,有這樣一幅照片:年輕的傅涯坐在一個小登上,嘴里叼著夾子,正在給女兒梳頭,天下的母親在這個時候,慈愛的神態(tài)都是一樣的。
我是在1950年初出生的,是我家孩子里生下來最大的一個,有8斤重。因為到了那個時候,部隊已經(jīng)打過了長江,我媽的生活條件也達到她結(jié)婚以來最好的時候:在跟著部隊走時,她相對沒有什么任務;而部隊繳獲的物資也越來越豐富,營養(yǎng)就跟上了。
我哥哥生下來的時候很慘,那時候我媽媽在延安,條件很艱苦,就是靠紡線,做些活兒能換點錢,然后是我爸爸有一點點津貼,用這很少的一點津貼,去換點羊骨頭來煮湯。于是我爸爸就去“騙”些吃的,我爸就有這個本事。聽我媽說,當時延安有幾個老大姐,其中有后來全國總工會的陳少敏,我們都叫她陳媽媽。我爸知道陳媽媽窯洞里有紅棗,有紅糖,趁他們不在時就去拿。結(jié)果剛偷到,人家回來了。他趕緊爬到床上把被子一蓋藏了起來,但還是被抓了個正著。老戰(zhàn)友們后來說,一進門一看那架勢,就知道肯定是我爸爸在搗鬼。然后,還是笑著把東西都給我爸爸了。
可是,回來后我媽還是沒吃成。東西剛拿回來沒兩天,就有一批負傷的老同志回延安來養(yǎng)傷了。我爸爸就跟我媽媽商量,說這個能不能給他們?nèi)パa身體?這些紅棗啊,核桃啊什么的都送給傷員了。所以,后來我哥哥生出來很瘦小,缺鈣。我媽就整天帶著他曬太陽補鈣一后來我哥哥開玩笑說,他長得那么黑,就是媽媽給曬的。
當時就在那樣的條件下,我家的孩子還特別多。因為我爸特別喜歡孩子,而且見了孩子就用胡子扎,得了個外號叫“胡子爸爸”,我媽媽就順理成章當上了“胡子媽媽”。有姐弟倆,當時他們的父母被我爸爸派到在日本人那里做情報工作,后來犧牲。兩個孩子被接到延安來上小學,每到周末時都是我爸爸媽媽給接回家,說這是我的孩子。男孩子跟我爸爸睡炕的一頭,女孩子跟我媽媽睡炕的另一頭。解放后家里孩子就更多了,有烈士子女。父母在外地外國的,像宋任窮叔叔家的兩個孩子,云南起義的盧漢將軍的女兒等,小時候都是在我家,一到周末,大大小小的孩子十來個,可熱鬧了。
我媽媽在家里的時候女紅就特別好。做衣服啊,織毛衣,做飯啊,樣樣拿手。我當兵以后在到南京軍區(qū)碰到一些父親的老戰(zhàn)友家的阿姨告訴我,當年他們在太岳區(qū)時,家里孩子都穿過我媽做的衣服、織的毛衣。我爸爸一看見誰家生了孩子,就說,去找傅涯去,讓她給做衣服。因為那會兒的女同志,一般都不太會這些活兒,全是我媽媽教會的,我媽織毛衣的本事特別大,她能一邊行軍一邊織毛衣,甚至一邊打瞌睡一邊織毛衣。
理想支撐一生
1961年3月16日,在戰(zhàn)爭中積勞成疾的陳賡大將在上海病逝。享年58歲,當時的傅涯只有43歲。在去世前,陳賡已經(jīng)預感到不好,他對傅涯說:“我有兩件事怕你經(jīng)受不起,一、我要死了!二、你的更年期過不好。”即便此時,他仍不改幽默本色:“你的頭發(fā)會‘唰’的一下就白了!”
司以想見陳賡的去世對傅涯是怎樣的打擊。
我爸爸剛?cè)ナ赖臅r候,我媽媽連我們那個家都不愿意回。她說,這個房子是部隊的,而她是組織部的人,要住到組織部去,不能住那么高標準的地方。最后被她的老首長羅瑞卿痛批了一頓才回去的。
爸爸去世以后,媽媽開始整理我爸爸的遺物,特別是他的日記。這些日記本,有的是拿軍布,特粗的那種麻布包的皮。每次我爸出去打仗,我媽就給他準備一個筆記本。我爸出去打仗了就記日記,回來以后本一交,我媽媽一直保存得特別好。這些都是不許別人動的。文革的時候,她最擔心的是這些東西,所以一讓她下干校,她首先是把這些東西安置好才放心走。
到了她的晚年,上世紀的八九十年代,為了給我爸爸寫傳,她帶著《光明日報》的原總編穆欣叔叔去采訪,一家一家跑,都是我爸爸的戰(zhàn)友。那會兒帶一個小錄音機,回來后,她和她的一個老戰(zhàn)友,都是六七十歲的人了,一句一句地整理。這些踏踏實實整理出的資料,有一些在軍史上都是很珍貴的。1982年,《陳賡日記》出版,2003年,又得以再版。
我覺得這些是我媽媽一生的信念。她參加革命后,工作上非常要求自立,但在感情上,她非常重視我爸爸的這份精神財富,這花了她一生的心血。也可以說,是她的精神支柱。
在她晚年精神上的另一個慰藉,就是臺灣的親人。她兄弟姐妹共有10人,其中有6個去了臺灣。最早,是從地下黨傳來過消息,知道他們在臺南。后來基本上都在臺北了。后來就沒了音信,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他們這些人也因為我們家受了很多苦。有的人被當作“匪眷、匪特”關(guān)起來,沒進監(jiān)獄的,也一輩子打入另冊不得重用。而在文革中,我媽媽因為這些臺灣的親戚,也被當成“特務”來整。后來,在改革開放后,我的這些姨和舅舅陸續(xù)回來探親,我媽媽也為此去美國和臺灣,與他們會面。她才知道,我外公去世的時候,曾對子女說,“找一個壇子,把我的骨灰放進去,放到海邊,漂回大陸。我得落葉歸根。”——這種骨肉分離也挺殘忍的。我的三姨和四姨是雙胞胎,她們重逢的時候,發(fā)現(xiàn),不但人長得一樣,她們連得的病也一樣。
我覺得我媽媽這一代人,他們腦子里理想是第一位的,骨子里頭就是一個共產(chǎn)黨員。有一天,我和我媽媽,去看望中組部的老副部長帥孟奇。帥媽媽解放前坐過國民黨的監(jiān)獄,文革中又被關(guān)了起來。我媽媽問她:“挨打了沒有啊?”帥媽媽的回答更有意思:“你說共產(chǎn)黨的還是國民黨的?”我媽媽說,“當然是咱們的了!”——我覺得在她們心里是這么一種感覺:她們不會為了這種冤屈而對自己奉獻一生的理想有絲毫的懷疑。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