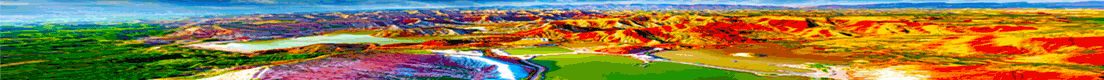“九一八事變”爆發(fā),日本人侵占東北,全國人民群情激昂,紛紛要求政府與日本絕交,對日宣戰(zhàn)。他卻于此時站出來唱低調,潑涼水,主張冷靜應對,與日本直接交涉,為了保全東北主權,不惜屈辱地承認日本開列的五大條件。
這不是漢奸是什么?
1933年,日本人打到熱河,對華北虎視眈眈,有血性之士著文號召與日本一拼!而他,卻拍案而起:“如果這才是救國,亡國又是什么?”“如果這叫做作戰(zhàn),我情愿亡國,也不愿學著這壯語作戰(zhàn)!”
兩年后,他居然跟侵略者日本勾搭,在日本報刊發(fā)表文章,提醒日本人不要輕視四億中國人的仇恨,不要因輕舉妄動而毀滅日本民族光榮的過去和偉大的前途。
再兩年后,“七七事變”爆發(fā),全國軍民正待奮起抗戰(zhàn)之時,他竟同汪精衛(wèi)、周佛海、高宗武等人搞在一起,大唱低調,企圖盡最后的和平努力。以至于八月七日的南京中央國防會議上,國軍參謀總長程潛指名道姓大罵其為漢奸!
確實,這樣的人不是漢奸,誰是漢奸?
然而,這個漢奸對中國抗戰(zhàn)的貢獻,卻遠遠超過了許多慷慨激昂紙上談兵的“愛國”義士們。正是他,在國家危難之際,毅然放棄自己極端珍視的超然獨立地位,應召出任中國駐美國大使。他稱自己“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全部心力投入了爭取美國支持中國抗戰(zhàn)的工作。
拖美國下水,正是他早在1935年,即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的兩年以前,就已經定下的策略。這年6月下旬,他連續(xù)給當時的教育部部長王世杰寫了三封信,謀劃抗日策略,并托后者轉達蔣介石。他對世界局勢作了兩個基本判斷:
第一個判斷是,在最近期間,日本獨霸東亞,為所欲為,中國無能抵抗,世界無能制裁,這是毫無可疑的眼前的局勢。第二個判斷是,在不很遠的將來,太平洋上必有一場最慘的國際大戰(zhàn),可以作我們翻身的機會,可以使我們的敵人的霸權消滅。這也是不很可疑的。
以此作為基點,他提出兩個可能的方案。第一個方案是與日本公開交涉,作有代價的讓步,解決一切懸案,原則為換取十年和平,爭取時間解決國內武裝割據,同時發(fā)展經濟,整軍備武,積累本錢,以便在將來的國際大戰(zhàn)中一舉翻身。
“倘辱而不能全,不能得十年的和平,則不免于一戰(zhàn)。”于是有第二個方案的提出,此即苦戰(zhàn)四年的計劃。
苦戰(zhàn)的目的,不是憑中國自身實力獨自戰(zhàn)勝日本,而在于加速那個“不很遠的將來”的國際大戰(zhàn)的實現,促使中日戰(zhàn)爭演變成國際大戰(zhàn)。他指出:“只有這樣,可以促進太平洋國際戰(zhàn)爭的實現,也許等不到三四年,但我們必須要準備三四年的苦戰(zhàn)。
兩年之后,歷史正好按照他這里所設想的第二方案展開,而這其中,也有他本人做出的不懈努力與不小的貢獻。
然而,最令人感佩不已的,還不是他的預見力,而是他對國家民族極端負責任的精神,是他在群情洶涌主戰(zhàn)的時候敢于主和當“漢奸”的勇氣。
與汪精衛(wèi)相比,他毫無爭權奪利的私心,也不像汪精衛(wèi)那樣對中國前途悲觀失望。對于中國最后的翻身,他始終充滿信心。1935年,在舉國趨于消沉之時,他公開站出來,呼吁大家反對華北特殊化,以致被日本軍方視為“一二·九”學生運動背后的黑手。當抗戰(zhàn)全面展開,中國人已經付出慘重代價之后,他更是成了堅決的主戰(zhàn)派,正式與汪精衛(wèi)分道揚鑣。因為代價已經付出,只有堅持到底,才不致前功盡棄。當汪精衛(wèi)發(fā)出艷電投向日本懷抱之時,他卻提醒政府,現在是和比戰(zhàn)難百倍,我們已經逼上梁山,除了苦撐待變,別無他途。
這就是他,一位曾經遭人唾罵的漢奸,一位真正的愛國者。
他的名字叫胡適。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