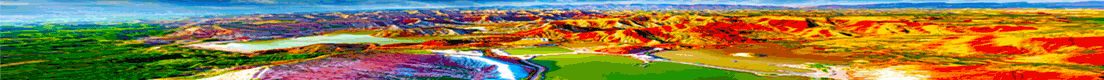當(dāng)社會目睹違法行為麻木不仁甚至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這些違法行為就會逐漸變成社會的潛規(guī)則,甚至進(jìn)一步變成顯規(guī)則,結(jié)果必然是有法不依,黑白是非不分,公平公正蕩然無存。
清朝咸豐八年(1858年)為干支紀(jì)年的戊午年,這一年正逢首都順天府(北京)的鄉(xiāng)試(考中者為舉人),主考官是協(xié)辦大學(xué)士(從一品)、軍機(jī)大臣蒙古正藍(lán)旗人柏葰,副主考是戶部尚書朱鳳標(biāo)和左副都御史程庭桂。八月初八日鄉(xiāng)試一開場,即謠傳在考場所在的貢院大堂發(fā)現(xiàn)了大頭鬼,據(jù)傳貢院中的大頭鬼不輕易出現(xiàn),出現(xiàn)一定有大案將要發(fā)生。九月十六日發(fā)榜,前十名中赫然見旗人平齡,他是一位著名的京劇票友,經(jīng)常登臺演出,因而引起輿論大嘩,質(zhì)疑優(yōu)伶居然能高中舉人。十月初七日,御史孟傳金上奏咸豐皇帝,參劾此次鄉(xiāng)試有舞弊行為,特意指出“平齡朱墨不符”。為了防止考官認(rèn)出考生筆跡從中舞弊,清代科舉考試規(guī)定考生親筆所寫的試卷用墨筆,然后指定人員用朱筆照抄呈送考官批改,“朱墨不符”即意味著平齡的試卷已經(jīng)被篡改或調(diào)換。咸豐命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戶部尚書全慶、兵部尚書陳孚恩會審此案,戊午科場案就此開場。
平齡被提審,但不久即死于獄中。等重新勘察平齡的試卷后,竟然發(fā)現(xiàn)其墨卷內(nèi)的草稿不全,朱卷內(nèi)也有七個錯別字曾被人改動過。十月二十四日,此次鄉(xiāng)試的全部試卷在 圓明園的九卿朝房重新勘察,發(fā)現(xiàn)“本年鄉(xiāng)試主考、同考荒謬已極”,有錯誤的試卷竟然有多達(dá)50多本,甚至有一人的試卷錯別字達(dá)三百多字,竟然也中舉。咸豐聞訊大怒,立即將主考官柏葰革職,朱鳳標(biāo)和程庭桂解任。諷刺的是,就在此次鄉(xiāng)試結(jié)束不久的九月,柏葰升任正一品文淵閣大學(xué)士兼軍機(jī)大臣,清朝只有大學(xué)士兼軍機(jī)大臣謂為“真宰相”,是真正的位極人臣。
隨著案情的深入,柏葰直接卷入舞弊的證據(jù)浮出水面??忌_鴻繹通過同鄉(xiāng)兵部侍郎李鶴齡的關(guān)系,結(jié)識了同考官浦安;浦安又通過柏葰的看門人靳祥的關(guān)系,請求柏葰同意調(diào)換羅的試卷使其中舉。事后羅又向柏葰、浦安行賄。咸豐九年二月十三日,載垣等人向咸豐匯報案情及處理方案,擬將柏葰“比照交通囑托,賄買關(guān)節(jié)例,擬斬立決”。由于柏葰是咸豐的愛臣,因此咸豐想替他開脫,但“諸臣默無一言”無人附和,而戶部尚書肅順當(dāng)場力爭,認(rèn)為科舉是國家選拔人才的重要制度,應(yīng)該嚴(yán)格執(zhí)法,才能改變科場上由來已久的惡習(xí),力主將柏葰明正典刑。在此情況下,咸豐認(rèn)為柏葰“情雖可原,法難寬宥”,同意將他“斬立決”,但咸豐很痛苦,“言念及此,不禁垂淚”。隨即同案犯浦安、李鶴齡、羅鴻繹與柏葰一同四人被押往菜市口斬首,此事震動朝野。有清一朝,極少有正一品大員被公開處斬,罪大惡極如和珅也僅是被賜自盡,連柏葰本人也認(rèn)為皇帝會下旨特赦改為發(fā)配邊疆效力,因此甚至還備好了行李,沒想到等來的竟然是執(zhí)行斬首的命令。
戊午科場案并未隨柏葰四人被殺而終結(jié),案情還在進(jìn)一步發(fā)展。在之前的審訊中,浦安供稱他聽說副主考程庭桂曾燒毀過請托者遞送的條子,程庭桂因此被捕,招認(rèn)他的兒子程炳采接到過幾個人的條子,都是通過幾位高干子弟的關(guān)系轉(zhuǎn)送的,其中竟包括了參與審案的兵部尚書陳孚恩的兒子陳景彥。這些請托者和遞送條子的高干子弟全部被捕,咸豐九年七月全案審結(jié),載垣等擬將程庭桂、程炳采父子共同斬首,咸豐念及程庭桂是兩朝老臣,不忍將他們父子一起處死,法外開恩將父親程庭桂發(fā)配軍臺效力,兒子程炳采仍然處斬,案中的請托者七人寬大免死發(fā)配新疆,戊午科場案至此結(jié)束。
順治、康熙年間也爆發(fā)過兩起科場案,所有考官都因舞弊被處斬。但到了平庸衰世的道光年間,官場秉承“多磕頭、少說話”的原則,沒有人敢批評時政,官員們在庸碌度日的同時卻也不忘腐敗。在這樣的背景下,科場當(dāng)然也難幸免腐敗,遞條子走后門蔚然成風(fēng),考官也不以收條子為恥,甚至以收到條子多為榮,已經(jīng)完全忘卻了這些行為是嚴(yán)重的犯罪。咸豐即位后,整頓吏治以糾正道光朝的腐敗風(fēng)氣,依法處理科場案,竟將當(dāng)朝“真宰相”公開處斬,這不啻是一記晴天霹靂,此后科場風(fēng)氣得到徹底扭轉(zhuǎn),無人再敢以人頭試法。
戊午科場案不只是一個亂世用重典的故事,耐人尋味的是它反映了當(dāng)有法不依,法律條文成為一紙空文,人們對嚴(yán)重的罪行麻木不仁后導(dǎo)致的人心、風(fēng)氣的變化。作為工作勤懇、謹(jǐn)慎、周密而深得皇帝賞識、器重的一品大員,柏葰事后只接受了浦安16兩銀子的酬謝,因此他肯定不是為了貪圖這區(qū)區(qū)16兩銀子而以身試法,他是囿于人情世故調(diào)換考卷以便關(guān)系人中舉,他肯定認(rèn)為這種行為已經(jīng)習(xí)以為常,因此自己的行為并無不妥。柏葰確屬罪有應(yīng)得,但他又何嘗不是腐敗風(fēng)氣的犧牲品呢?當(dāng)社會目睹違法行為麻木不仁甚至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這些違法行為就會逐漸變成社會的潛規(guī)則,甚至進(jìn)一步變成顯規(guī)則,結(jié)果必然是有法不依,黑白是非不分,公平公正蕩然無存。
(責(zé)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