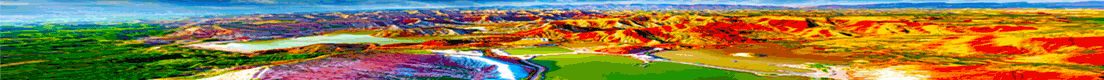漫漫黃沙,寂寂戈壁,莫高窟和守護(hù)著它的人遍歷這里每一個寒暑春秋。76年間,一代代知識分子遠(yuǎn)赴大漠深處,接續(xù)守護(hù)莫高窟,瘡痍之地逐步成為世界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的典范,“吾國學(xué)術(shù)之傷心史”成為過去,世界敦煌學(xué)的中心冉冉升起。

敦煌研究院工作人員對莫高窟152窟進(jìn)行數(shù)字化采集(2014年9月1日攝)。
初心不悔為敦煌
他裹著羊皮大衣,頭戴老農(nóng)氈帽,呼吸的熱氣迅速結(jié)成冰花,蜷縮著像是“沒有生命的貨物”。西去敦煌時,常書鴻還不到40歲。
此前,他是留法9年的藝術(shù)家、北平藝術(shù)??茖W(xué)校的教授,西裝筆挺,風(fēng)度翩翩。塞納河畔的一本《敦煌石窟圖錄》讓醉心油畫的他為中國藝術(shù)傾倒,家國破碎戰(zhàn)火紛飛更讓他心系敦煌。
1944年,“國立敦煌藝術(shù)研究所”在大漠中創(chuàng)立。那時,莫高窟已荒廢400余年。流沙從崖壁頂部傾瀉而下,上百個洞窟被掩埋。壁畫大塊大塊跌落,砸爛在地上。
破廟當(dāng)辦公室,馬廄做宿舍,水里的泥漿澄清了就拿來喝。最可怕的是孤獨(dú)。帶病的同事含淚對常書鴻說:“我死了以后,可別把我扔在沙堆中,請你把我埋在泥土里呀!”
初創(chuàng)者接連離開,妻子也棄他而去,常書鴻卻初心不悔。“我如果為了個人的一些挫折與磨難就放棄責(zé)任而退卻的話,這個劫后余生的藝術(shù)寶庫,很可能隨時再遭劫難!不能走!”
段文杰、孫儒僩、歐陽琳、李承仙、史葦湘……在常書鴻的全力招募下,一批批大學(xué)生告別優(yōu)渥的生活,奔赴大漠。舊照片見證別樣青春:穿旗袍的女孩和穿白襯衫的男孩,乘坐的卻是一輛破舊的木輪老牛車。
他們幾乎用雙手清除了數(shù)百年堆積在300多個洞窟內(nèi)的積沙,修建了千余米長的圍墻。臨摹缺紙就用窗紙自己裱褙,毛筆禿了拿小刀削尖再用,連顏料也是自制的。
一個冬日的下午,敦煌研究院首任接待部主任馬競馳走進(jìn)院史陳列館,在小院里回憶起幾十年前的生活:這里養(yǎng)過雞,那里理過發(fā),聯(lián)歡會上的歡聲笑語歷歷在目。“沒人喊苦,也沒人叫窮,日子就是這么過的,大家高高興興干工作。”
眼前不見苦,只因宏圖在心中。

時任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在查閱資料(2014年9月2日攝)。
勇?lián)厝慰复笃?/div>


起初是白手起家斗流沙。到了20世紀(jì)80年代,莫高窟人面臨的課題則更嚴(yán)峻。有人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xué)在國外”,他們怎能甘心?
國家將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為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長段文杰重任在肩。沒有高談闊論,他只說守著莫高窟的人首先要有作為。“要靜下心來,埋頭苦干,最后讓成果說話。”
一個初冬的早晨,馬競馳去段文杰的房間,看到他一口氣吃了6個大大的香水梨,很是不解。段文杰解釋說:“梨解渴頂餓,不用下來上廁所,在洞子里能一直待到太陽偏西。”為了臨摹一幅《都督夫人禮佛圖》,他翻閱了100多種資料,摘錄了2000多張卡片。
《敦煌研究文集》《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以及《敦煌研究》期刊……20世紀(jì)80年代,滿懷愛國心的一代莫高窟學(xué)人奮力拼搏,用豐碩的學(xué)術(shù)成果扭轉(zhuǎn)了“敦煌學(xué)在國外”的局面。
段文杰力倡接軌國際。去年辭世的敦煌研究院原副院長李最雄曾回憶:“段老深知文物保護(hù)工作的艱巨。要做好莫高窟的保護(hù)工作,必須走學(xué)習(xí)國外先進(jìn)技術(shù)的捷徑。年輕人被送出國深造,光是去東京藝術(shù)大學(xué)的就達(dá)70多人次。”
1998年,年近60歲的樊錦詩被任命為敦煌研究院院長。退休的年紀(jì),她卻重新站在了起跑線上。
游客太多,她日夜揪心。“不讓看不行,看壞了更不行。哪能一味想著門票和鈔票?”于是,莫高窟在我國的文化遺產(chǎn)地中率先進(jìn)行文物數(shù)字化探索和游客承載量研究,“數(shù)字敦煌”項目讓莫高窟“永葆青春”成為可能。
她說“不能頭疼醫(yī)頭,腳疼醫(yī)腳”,便推動制定了《敦煌莫高窟保護(hù)總體規(guī)劃》。在她的持續(xù)呼吁下,甘肅制定專項法規(guī)《甘肅敦煌莫高窟保護(hù)條例》,莫高窟有了“護(hù)身符”。

游客在莫高窟數(shù)字展示中心排隊等待參觀(2016年8月4日攝)。
開拓進(jìn)取求創(chuàng)新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古絲路重鎮(zhèn)敦煌再度吸引世界的目光。“古絲綢之路孕育了敦煌。我們在歷史中尋找未來,以文化交流促進(jìn)民心相通。”故宮博物院院長、敦煌研究院原院長王旭東說。
去伊朗、去阿富汗、去吉爾吉斯斯坦……敦煌研究院的學(xué)者走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自美國、日本等國的研究人員扎根敦煌,循著古老壁畫探尋文明交流的印記。
2019年11月,我國首個有關(guān)文物保護(hù)的多場耦合實驗室在敦煌研究院竣工,長時間降雨、降雪、刮風(fēng)等自然條件得以在實驗室模擬。“文物保護(hù)進(jìn)入深水區(qū),要攻關(guān)的都是難解決的問題,研究要向縱深方向去。”敦煌研究院保護(hù)研究所所長郭青林說。
敦煌也在變得年輕可愛。新一代莫高窟人攜手科技企業(yè),讓敦煌文化以流行音樂、游戲、漫畫等形態(tài)“飛入尋常百姓家”。
干了20多年講解工作,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揚(yáng)部黨支部書記宋淑霞“轉(zhuǎn)換賽道”設(shè)計起研學(xué)課程。“孩子們穿上仿唐代半臂襦裙,走進(jìn)壁畫修復(fù)現(xiàn)場,深度感知莫高窟。希望敦煌的種子能在他們心中生根發(fā)芽。”
敦煌研究院院長趙聲良說,回顧研究院70余載歷程,發(fā)展的根本在一個“人”字。前輩奠基、大家關(guān)注、一代代人甘坐冷板凳,敦煌文化的保護(hù)、研究、弘揚(yáng)工作才得以步步向前。愿更多高端人才走進(jìn)莫高窟,在千年敦煌找尋新天地。(完)

敦煌研究院技術(shù)人員在莫高窟98窟內(nèi)對病害壁畫進(jìn)行修復(fù)(2014年9月3日攝)。
新華社記者張玉潔
(責(zé)任編輯:張云文)
新華社記者張玉潔
>相關(guān)新聞
頂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