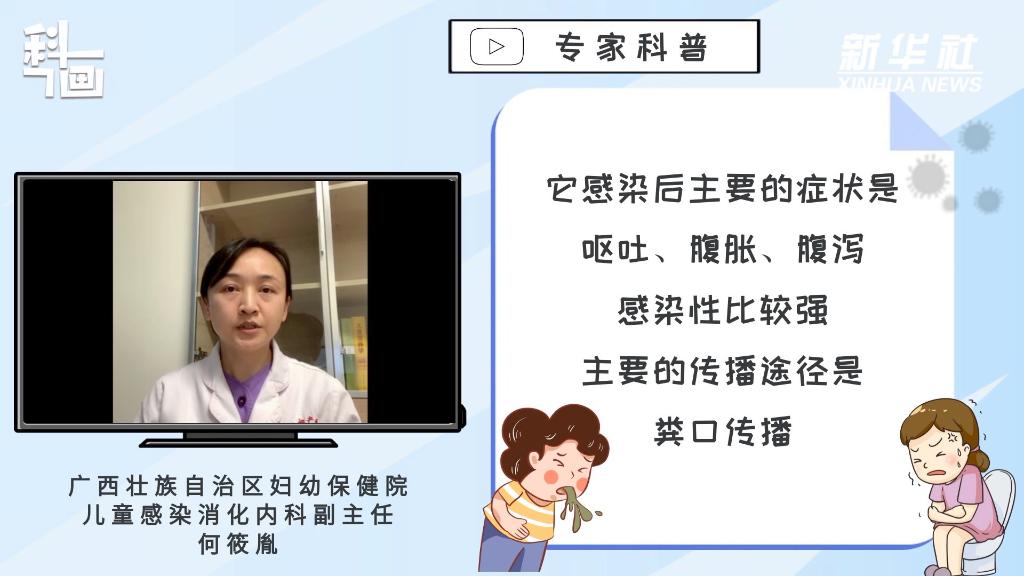高海軍速寫
高海軍,男,出版人,當代畫家。早年畢業(yè)于西北師范大學美術(shù)系,分配至“讀者”雜志工作多年。后調(diào)入中國青年出版社。

高海軍素描柳宗宣
柳宗宣,詩人,散文作家,曾任中國青年出版社《青年文學》雜志編輯多年。2009年南遷湖北武漢,供職于某大學新詩研究所。2018年自筑山房,現(xiàn)居漢口和大崎山兩地。
游動沙龍——我與海軍:北京生活敘事
墻面遷徙的葫蘆
那有兩只葫蘆的靜物油畫掛在看云山房一樓客廳。在下樓時常望見它,兩只葫蘆在綠色畫面中間,一只肉肉的坐立,根蒂彎曲朝上。另一只,側(cè)伏于旁,保持若有若無的距離。藍色的背景襯著葫蘆的身子的曲線和黃色表面的暗瘢,被鑲進有層級的木頭褐色畫框內(nèi)。
之前,它掛在北京東六環(huán)邊的皇木廠院墅一樓的客廳。在北方皇木廠的房子內(nèi)掛陳多年后,隨我南遷至武漢,在漢口公寓客廳停駐多年,九年后,又隨我遷入山嶺墅院。
它曾被打包物流在駛往南方的火車上;某個時辰,在汽車后備廂隨我到達山間墅院。陳列在不同的時空的觀看,喚醒交錯的回憶的目光。樸素日常的葫蘆被描繪、被呈現(xiàn)。停歇或轉(zhuǎn)徙,參與了你生命不定的游走。肉肉的葫蘆挺立于畫布,還帶著生命脆弱的顫抖。

柳宗宣的看云山舍外景
2005年某個夏日。北京宋莊畫畫的哥們騎著摩托背著這幅畫,駛向我正在裝修的皇木村的院落。
他聽說我的北漂生活轉(zhuǎn)好,擁有了自己的房子,將它送來作為我喬遷之喜的賀禮。他叫賀天,是我在宋莊居住時認識的,曾到過他購買的農(nóng)民的房子將之整修一新的庭院。畫室。落地玻璃窗可見院中水池。院子掛著一個個葫蘆。他將其日常風物轉(zhuǎn)入畫布。
初到北京被介紹到宋莊,感覺親近,就租入了農(nóng)民劉殿元的院子。見到來自全國各地的畫畫的走動在京東村莊的道上,長發(fā)。褲頭上染有炳??;隱在一個個紅磚院墻內(nèi)空闊的畫室和簡易的書房里;他們從各省奔赴于此,成群聚集。畫廊。餐廳和酒巴。家庭讀經(jīng)會。將一個個土不拉機的鄉(xiāng)村弄成了有炳稀氣味或搖滾歌聲回蕩的村落;被小麥子和白楊樹環(huán)繞小埠、大興莊被改造成了類似于紐約的1963年的格林尼治村。熱愛藝術(shù)的人,來自不同省城攜著不同口音和經(jīng)歷,將此當成民主生活的實驗室。
群居者在此營建他們?nèi)绺?滤漠愅邪?。隱隱依傍近六十里有公交車可以到達的首都,在此重建空間,落實他們的愛好;進進出出,在此過著等級不同的生活,如同不同大小或奢或儉的院落。那里不斷更新的的面孔和消失的背影。
那年,我成了一個不在單位領(lǐng)工資的人,愿意為藝術(shù)而流浪,成了類似于蒙帕納斯的流亡者;來此尋找新的節(jié)奏,在麥田和苜蓿地中間,建設(shè)工作室。尋求某種生活和精神上的自由感。在鄉(xiāng)村,選擇與狗、植物和自己生活在一起,深深地擁抱孤獨。獨居成為生活常態(tài)。宋莊畫家村的院門都是緊閉的。
后來離開了那里,到了京城中心。為了稻梁謀,到文學雜志做編輯。幾年后,2005年移居皇木村,想著如小說作家羅伯特·格耶住在距巴黎百多里的麥尼爾鄉(xiāng)村城堡;理解他為什么要住在距城那么遠的地方,把自己安置在邊緣,自然一點的環(huán)境中,雖然它被污水河環(huán)繞,但還有防風林,散步的地方,有原生林,帶院子的樓房。想著把過去繁華漕運碼頭遺留下村落----皇木廠,當成可能的靜修之所。在此安頓自己的圖書。葫蘆靜物油畫,作為禮物就這樣掛在了皇木村南五區(qū)六十三號的一樓的客廳。

柳宗宣京東六環(huán)邊的住宅
畫畫的同事高海軍曾到過那里。他為此寫上幾一段文字,收錄在他出版的書中。“詩人家的墻上掛著幾幅油畫,分別擺放在樓梯轉(zhuǎn)腳、客廳、書桌旁。油畫引起我的興趣,畫作不大,30cmx40cm,畫中景物并不復雜,是一個葫蘆,葫蘆擱置在桌子上,黑灰色的桌子隱匿在褐色背景里。有如莫蘭迪筆下的靜物畫——”
在那葫蘆的注視下,二十年前,北京初夏的某個中午,我和高海軍還有他的妻子,圍著西餐桌會飲。他不時瞅上幾眼那葫蘆畫。南北分離,時光阻隔。在山舍,葫蘆停駐在我的視線和回憶中。這遷徙的游動的葫蘆,仿佛恒定的某物以它的光將我們環(huán)繞,擢升、甚至寬恕。

柳宗宣上班途中(三里屯)路過的房子
葫蘆凝視他的歌唱
2000年,在北京東四十二條,我認識了高海軍,他是社里的美術(shù)編輯,我是出版社下屬的文學雜志的編輯。初識在出版社共商出版社發(fā)展高峰論壇會上。他剛從甘肅的《讀者》雜志調(diào)到中國青年出版社。他畫油畫,期刊美術(shù)設(shè)計從業(yè)多年,會上我仔細地聽了他的發(fā)言,覺得他是一個搞藝術(shù)的,沒有被職場所馴化,保持著他作為畫者的身份,這和他的身體語言是吻合的。他的發(fā)言和他的有絡(luò)紗胡子面容是相襯的,全無套話,出之于從業(yè)個人心得和專業(yè)上的體悟。他的發(fā)言不是很連貫或油滑,眾目之下的新來同事有點羞怯,或?qū)酃鉄羲频哪抗獠贿m應。我喜歡上這個長有絡(luò)紗胡子穿著軍綠色褲腿兩側(cè)有兜的哥們,在會間走廊上,我們相握彼此的手。他知道了我是寫詩的。
以后我們碰到一起背著他的凡布包匆匆進入出版社的院內(nèi)也要站在一起說上幾句。后來,我們的辦公室搬到了東直門浩鴻園,在同一層辦公。我時常竄到他的辦公室;他也到我們文學編輯部喝杯茶;有時我們在就餐后的空隙聊天,大都關(guān)于我們創(chuàng)作的事。他說他到了北京,總想著蘭州,想到在那里生活創(chuàng)作幾十年的大西北;回到那里,人的呼吸就通暢了。其實,我們處在相似的情境,初到北京,我們的創(chuàng)作按上了暫停健。想著當年,一個中年男人(四十歲)到了北京,一個人騎著車混在人流中到一個陌生的單位,懸置在高樓辦公室內(nèi),與過去鐘愛的給他帶來靈感的土地隔離,像弋壁上一棵胡楊樹被移植到京城的胡同,與西北的地氣隔離了。

我們在一起說笑、聊天。在京城,我們在營建屬于個人的空間。在有葫蘆靜物畫的房子,提及莫蘭迪,我們喜歡的畫家。酒興正隆,詩和畫可以助酒興,他的妻子在旁說,老高曾為知青文藝隊成員。在座的各位即要他來一曲——老高停下杯箸,抹了抹他的絡(luò)紗胡子,坐著,清唱。酒桌上變得安靜。那兩只葫蘆停駐在墻面,似在聆聽。
“一彎彎流水喲,一道道梁,一朵朵彩云下山崗
巧嘴的山雀雀喲,你咋不唱
牧羊的哥哥喲,酸溜溜的好心傷…
海軍即興歌唱的嗓音和呼氣——呈現(xiàn)大西北黃土高原味道。讓我重臨高海軍在畫中表現(xiàn)的畫境,以他的寬厚的嗓音和氣息吐納?;蛘哒f,他的歌聲從他的畫布傳遞過來,攜帶著畫面的風聲和云團飄移以及孤寂的肅穆——
云中人-大巴上
作為《青年文摘》雜志美術(shù)總監(jiān)的高海軍對文學有著某種親和感,他常向我談及我編輯的某某的文章可讀。漸漸我將他當成同道,時常聚在一起天南海北的。某日。在我們用完午餐回到辦公室路上,海軍聊起了他早年寫生的往事。在編輯部的樓下花壇的木椅中坐下,聽他細說。
某年秋天,他和友人到甘南尕海鄉(xiāng)的西倉寫生。在山谷,他仰望藍天,看著大朵白云飄過,他沉浸在白云與天空構(gòu)成的飄忽的空闊中。在一個大草坡上,一朵巨大的孤云向他移來,清晰逼真,仿佛要飄落下來了。山坡上長滿雜草和樹木,無人寂靜的坡地,只有風吹拂的靜寂,翻動著樹的葉片的反面。

高海軍早期作品:回聲
這時的他,忽然看見白色云朵正中間,出現(xiàn)穿灰色長衫的人,向他“唉唉”地打招呼。他以為是幻覺,眨了眨眼,再看上去——逼真的視界中,確實有一個穿長衫的人立在云端上,向他發(fā)出呼叫的聲音,不緊不慢,他清晰地聽到了。
他垂問我,云朵中的那個人,是不是他的另一個自我,或他早逝父親的靈魂的回返?
與云中人邂逅后,他發(fā)現(xiàn)心境若止水的平靜。然后,看著那片孤云和云中的那個人影緩緩遠去。遺棄了他,風聲隨之消逝。
你可以把這個片斷寫下來。高海軍按照我的建議,如實寫下他在外出寫生的一些往事片斷。我對他說,陳述你個人真實現(xiàn)場不要直白評議;再現(xiàn)其細節(jié)、放棄自白。他努力按我的意思去做,以文字來陳述。我也感動于他對文字的熱愛,理解他的情感和心思,將其梳理刪減,編入雜志的《詞與物》欄目中。從此,他和我建立了某種以語詞為媒介的信任感。啟發(fā)他在繪畫語言之外,如何用漢語來呈現(xiàn)色彩不同呈現(xiàn)的存在,表現(xiàn)繪畫的意圖和起念與作品成型的過程。從此,他的隨筆寫作一發(fā)不可收拾。
2006年秋,出版社組織秋游活動。從山西回北京的大巴上,海軍坐在我的身旁,躺靠在軟質(zhì)大巴的可以調(diào)置方向的沙發(fā)上。在大巴后最后一排上,我們慵懶無事,長一句短一句的閑聊。詩和畫,男人與女人。
我發(fā)現(xiàn)大巴上前坐的女人:嬾嬾的樣子,樸素天然得沒有一絲做作。出門集體旅行讓她變了服裝,頭發(fā)做了處理。青春的風韻,溫和的氣息,天真的嬌媚,從她的身體顯示出來。單位那么多女性你為何沒有留意,反而在意到這個在食堂打著零工的女子。她沒有受過多少的教育,這來自東北小鎮(zhèn)的離異女子。她曾說她六年前到的北京,通過人介紹找了個北京男人,日子過得不順,又無意被人引薦到這里來做事。你總是看見她在食堂少言少語地做活。她和我見面時只禮貌地點點頭,也無多余的笑。無機心,無勢利眼,沒有過分修飾后的造作(上天賦給她的資色是什么就是怎樣),沒有因世俗生發(fā)的過多的分別心;沒有對生活過分的追求;沒有因生存的艱難而使她性情變得暴戾,反倒讓其持存悲憫心。在人面前不低眉折身也不揚眉瞬目。她的理性建立在她感性上;她的美感來自上天賜給她的身體與容顏。這民間的女子,散逸著自然母性的光暈,忽然間約翰-克利斯朵夫眼中的薩皮納這個人物,從心里給喚醒;薩皮納在你心中存活多年的形象,轉(zhuǎn)移到了她的身上。
我把目光從她身上移開,又投向窗外太行山腳平地中抽穗的高粱。在平鋪開來的傍晚的光線中,折射出莫名的令人喜悅的光影和美色。大巴正駛過太行山區(qū),向北京城區(qū)駛?cè)搿?/div>









(責任編輯:張云文)
沉默了一陣子后,我和他提及那個有葫蘆的油畫。不自覺談及文藝復興時期的佛拉芒繪畫。那是一場藝術(shù)革命:個體進入圖像;畫者關(guān)心的不再是圣經(jīng)中被神圣化了的人物與事件。而是我們進走家門碰到的普通人。如此,肖像繪畫演變成關(guān)于個體的頌歌。由此我自然提及十七世紀的荷蘭繪畫,那也是學者托多羅夫論及過的,繪畫中的主體性的出現(xiàn),畫者大膽選取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通平庸甚至低等的事物納入畫布,將日常流轉(zhuǎn)無常的東西凝定成為持久的東西,由此體現(xiàn)藝術(shù)對變幻無常稍縱即逝的日常生活的勝利。如德-霍赫的畫中描繪的家庭生活中的母親,日常行為本身獲得某種幾近神圣的特征。
繼而我談及他的繪畫有著印象派畫家們的各種技藝使用。比如他的描繪云朵的畫有著德加畫中所追求的旋律和樂感;但有的畫作也有著凡高的強烈的抒情性甚至神性元素的加入,雖然也有著東方本地地域元素的加入,但總的色彩氛圍是抒情。
進而,我提及到了馬奈的畫,那幅被??略谠L問突尼斯時演講過的馬奈的畫《陽臺》。在那畫中,可見性與不可見性在觀畫過程中,如何得以變化與置換,我向他轉(zhuǎn)述了福柯所做的結(jié)構(gòu)主義與文學分析;自然涉及福柯對另一個畫家馬格利特論文:《這不是一只煙斗》。圖形與文字之間的依存與分離——那畫面中出現(xiàn)一個不確定的模糊區(qū)域?,F(xiàn)代繪畫所呈現(xiàn)出主客觀的交互關(guān)系,指向哲學向度的思索——當我們神游式的交談漫游至此,大巴駛?cè)霟艄忮e落繁雜的京城。

柳宗宣在他主持的采風活動現(xiàn)場
被云朵塑造的畫者
高海軍的早期繪畫以及關(guān)于繪畫的文字,皆涉及西部土地。在一則文章中我這樣寫過:他出生在那里,求學在那里,讀書在那里,寫生在那里,大部分重要作品完成在那里,生活與創(chuàng)作的記憶留存的那弋壁沙漠,高原梁峁,河西走廊的坡地,烏鞘嶺八月開放的油菜花——那片土地給他創(chuàng)作的靈感與意象,關(guān)于創(chuàng)作的最大的享樂在那里獲得。
他的畫就像芨芨草是在那片土地上生長出來的,在我看來,那片天空田野和山嶺,與他是相互給予相互成就的。高海軍八十年代的所有作品和寫生都是關(guān)于西部那塊土地的:祁連山腳的皇城草原,甘南黃河源頭的海子邊,隴東涇川他少年與父母借居的楊柳灣、他插隊時住過的河西走廊戈壁灘上知青點,蘭州市郊的青白石,黃河水從銀灘大橋流過的場景,等等這些都保留在高海軍的素描與油畫寫生里,他的繪畫從那片土地上采集了意象,是那片大地上的風物讓他產(chǎn)生了描繪它們的欲望,情不自禁地在那片大地上獲得色彩與構(gòu)圖,那片土地給他作為一個畫者最好的禮物,或者說它成就了他。
在大西部的天地之間,高海軍受到了自然給他的最好的教育,那片蒼茫荒涼而生生不息的土地,讓一個創(chuàng)作者震驚,感應那宇宙的能量,從而獲得天地謙遜無言的大美,并保持了一個修行者高貴的緘默。如果說,大西洋的原始的塔希提成就了畫家高更,也可以說河西走廊的上空的變幻多姿的云朵成就和傳遞著高海軍系列作品《回聲》,那畫布里回蕩的靜穆與肅然。
“每每置于那片自然的曠野,心靈瞬間被沉厚和博大充盈,感覺像在天上,吮吸著從天而降的信息——曠野里的傳來的風聲,經(jīng)過戈壁灘仿佛風神從遙遠處的呼喚,我猜測那是來自宇宙的秘密。”高海軍在他的著作《步行者》中的獨白道出了一個訊息:他是把那片土地那里的風物當成一個神奇的存在看待的,那里的自然不僅讓他回歸自我,給他安靜和創(chuàng)作的能量,或提供一個觀察、共同創(chuàng)作的氣場,而且他將大自然當成他自己上帝的化身。在那里,他培養(yǎng)內(nèi)觀的能力,體驗著大神秘和宇宙的實在,獲得神的意象。這樣他的《回聲》系列作品里出現(xiàn)了神跡?;蛘哒f,他從無意識深處獲得直觀,發(fā)現(xiàn)內(nèi)心的神性,然后把這些直觀翻譯成他的繪畫作品,使他的作品神奇、寂寥、肅穆和深奧。
在他的布面油畫《行走》中那個巨大濃厚的白色中摻雜灰色的云團幾乎占去了畫面的一半的空間,云團下面一個喇嘛在行走,他身著的黃色袈裟幾乎與黃土地同色讓人難以辨認,畫面前方,云朵下一輪藍色月亮。這些元素共同營造了肅穆的神性的氣場。那個渺小得幾乎可有可無的喇嘛在行走。從中我們聽到來自人類的祈禱。
那幅木版油畫《回聲》中,高海軍用刮刀勾勒出來的那些蒼勁的樹干,樹木邊上的高坡和高坡頂點上的停泊的一團停止不動的白云,在高海軍著意要表現(xiàn)的是他感應中的自然和宇宙的奧秘,并能從他的繪畫里看見云朵柔軟與力量接合的推力。因了云朵在畫面的出現(xiàn),他的繪畫呈現(xiàn)出云朵般變幻的節(jié)奏繪畫語言的靈動,色塊的波動呈現(xiàn)出畫中的音樂。神秘的喜悅和五彩繽紛的意象,具有了動感音樂變幻的節(jié)奏與韻律。如他的卡紙作品,關(guān)于莫高窟的意象——畫面上明亮的銹紅色和深藍色還有一抹抹桔黃所構(gòu)成的色塊的舞蹈。我?guī)缀跏窃趦A聽這幅作品旋律。高海軍對色彩有著印象派畫家的專精,他畫中的色塊給我們制造出夢幻景色。他知道顏色的本質(zhì)有著如謎的內(nèi)在的力量。
高海軍繪畫里的構(gòu)圖基本意象:黃土高原的梁峁,畫面上的枯木,然后是這荒涼黃色大地之上的一片或一群云朵(有的畫面全是云朵,變幻不定的云朵,這離灰塵很遠離太陽最近的精靈),云朵間隱現(xiàn)他直觀到的人形。紀德有過類似的表述,“藝術(shù)是上帝與藝術(shù)家之間的合作。在這個合作中,藝術(shù)家做得愈少愈好。”從這一點看來,一個人的才華指數(shù)有多高,要看他和自己的泉源溝通連結(jié)的程度。這要求一個創(chuàng)作者蛻掉自身非本質(zhì)的表面附加物,那個回應外部世界、文化壓力和指令下發(fā)展起來的自我屈服于他的內(nèi)在本質(zhì),靈魂自性??梢哉f,高海軍是一個被云朵塑造了的畫家。云朵成了他特有的繪畫語言。那個云朵中的人影,在我想來,他與一個神秘存在的溝通,他將這種溝通轉(zhuǎn)化成了他的創(chuàng)作,在他生命的特殊情境下碰觸到了這神秘泉源。

高海軍作品
告別或重逢
在京呆了十個年后,準備離開,到南方一所高校去討生活。記得在三里屯那個十字路口,我對他說我就要回湖北了;和他提及另一個愿望,編輯一本自己的在意的書刊。我對他說,你要恢復畫畫,不然,太可惜了。我們外在的什么都有了,缺失的是將中斷的創(chuàng)作接續(xù)起來,保持藝術(shù)生命的完整,也就是說必須完成我們的信靠的詞語繪事生涯;不然會后悔也來不及的。他點頭稱是。

柳宗宣、高海軍、宮林在武漢木蘭湖
2012后,他出差到了武漢。想見見我,那年,我總算是料理了諸多外部事宜,人好象又活過來了,因為能重新回到如愿已久的創(chuàng)作中來,回到自己的書桌前。或者說,是將很多事向心外推卻。真正回復到幾乎中斷了近十多年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詩歌寫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一批新的作品不受控制的涌現(xiàn),感覺自己真正的活過來。恰逢這個時辰,他來到我生活的城市。我們重新在一起,還帶來了隨他同行的北京電影學院的宮林教授,在旅館里一見面,就朗讀我的新作當著他倆的面。作品屬于內(nèi)心的談話。海軍和他的朋友坐在旅館的那兩木椅上,椅子中間的香煙和茶杯。我坐在他倆對面的白色床單上,對著他們朗讀。海軍如多年前一樣在我面前聽著,偶爾為某個句子叫好。
我拿什么招待老友新朋。唯有以這些年發(fā)現(xiàn)的私已喜好的木蘭山水招待他倆。驅(qū)車帶領(lǐng)他們到漢口北的木蘭山水間。仙鶴島。半畝園。我們的交流在通往那片山水的路上展開。他們頻頻點頭,當白鷺隨著車內(nèi)的爵士樂而飛起。木蘭湖水清碧,在風中蕩起一輪輪微波,喚醒我們投入其中。我對他們說,山水確有某種治愈精神癥候的效應。在這山水間,寄宿。讀書。寫詩,城市在遠避,覺得自己在活著,當我們的車停在何家洼,我指給他們看:這里的茅廁都是用石頭砌成。它的低調(diào)的奢華。我對他們說,我愿走岐路,探入一個個寂寞荒蕪的小山村,似乎被遺棄;迷戀這里的頹廢之美。將車停駐路旁,遠望那遠橫亙前方的崇山疊巒,問詢他們:“——這不就是塞尚描繪的風物?;蛘哒f,倔強的老人將圣維克多山,綿延至此。這是你們的作品。用線條色塊情感構(gòu)建它們,幕天席地垂掛在這里。”
每到了北京我都去看他。我們的聚會加入了一個人:宮林。他聽說我到了北京,在他公寓附近預定好包廂,我和海軍前往。我們的談話在韓式料理的圓桌火鍋前展開。我們談及宮林兄教授的電影課。他贈我以他的圖書。海軍談及宮林的妻子的線描作品。時隔多月后,我們在海軍的宋莊的畫室聚會見到她,還有她先生的男女研究生也參與進來,我們的交談拓展了多維空間。
我留戀北京十年,在賣掉城中的公寓時,不舍那些年購置的家具什物,又在通縣購得一套復式樓安置它們,海軍笑著對我說,這是他可以理解的做事風格。房子在那里,友人在那里,你就有重返的理由。到過去生活的城市,總要見見海軍,以前就職的編輯部辦公室調(diào)變?yōu)樗诘碾s志。這樣,我去看他,他坐在我使用過多年的辦公室,使用著我過去用過的電話號碼。在那個交錯的空間,百感交集。我和他在一起,黑色的辦公桌前,大理石地面上,我們聚首,好象從未分隔。
東直門。浩鴻園。西壩河。如多年前,步行到達這里。經(jīng)過北京六三環(huán),多年前一樣,守在窗口,望望使館區(qū)樹木下的洋樓。農(nóng)展館。國際展覽中心。煤炭總醫(yī)院。我在詩文中寫過的槐花布滿路面;看見多年前的自己在710公交車站前等候;又碰到那些天橋上的乞討者。朝向海軍的辦公室,停駐在北方的天空下,仿佛看見他畫中的白云游蕩到馬路中間。他后期畫中的胡同和地鐵車內(nèi)的人群向我涌來,陌異又親切。

高海軍北京時期的油畫作品
他坐在我熟悉的黑色的辦公桌前等候,一見面我就談及這些。他要我看他的新作,要我加以點評。他抽著煙,藍色煙絲繞守我們相聚的頭頂。我注意到電腦中他設(shè)計的圖書封面。他身后的辦公書柜里擺著他新購的畫冊和人文類圖書。他編輯的刊物的藝術(shù)感在加強。他在此,或作用本地空氣的變化,這是一個良好的藝術(shù)家在職場的作用力。
他向我談及他早年在《讀者》雜志工作的情景:是夜晚燈光中,他工作時播放的樂曲環(huán)繞著他,還有他吐納的絲狀煙霧。這是他最佳工作狀態(tài)。他在給刊物平面設(shè)計,插圖隨著標題和內(nèi)容放置不同位置,又與前文的情感內(nèi)容構(gòu)成某種微妙呼應。在他看來,插圖也是創(chuàng)作,如同他手持畫筆和調(diào)色板在布面上即興創(chuàng)作或改動。
我看了看他,眼神發(fā)光。他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也得到了較好的恢復。辦公室里擺放出他的油畫作品。他拎出來讓我觀摩。他說他在宋莊有新置的畫室。當我前往他畫室的路上,在他的新車的副駕室有感而發(fā):藝術(shù)家必須對自己的藝術(shù)生命負責任,不可浪費虛擲到單位家庭人事的糾纏中,不可向外推諉,我們必須向內(nèi)反省,對自己提要求,傾聽內(nèi)心的呼聲。
他正在恢復創(chuàng)作。他試圖回返過去畫畫的狀態(tài)。居京畫畫不易,多種誘惑作用于人的身心;很多事讓人分不開身。我和海軍氣質(zhì)有些類似,低調(diào)行事,能忍受屈辱;他比我有更強的克制力和對舌頭的管轄力。偶爾我有地火升騰冒煙的失控。因為我是楚人,有著祖?zhèn)鞯墓⒅迸c火爆脾氣。但我們不舍對心中的眷念,總能聽從它的聲音指令。藝術(shù)它讓你必須放下塵俗的一些東西,為了取得一點成就或滿足感,你必須放下外在的一些東西;它要你全力以赴。放棄了外在名聲,把寶貴精力與時間用于藝的研習上。
在海軍帶有院落的畫室,我沉默了很久,當我看過他的一批新作后。海軍做得不錯,在十多年后的今天,看見他的油畫新作,真正為之感到安慰。過了五十歲我們中斷了一些年頭后還能重返畫室,是這哪輩子修來的福份。他在宋莊來安置一間畫室,試圖找回個人的孤獨,為了他的繪畫藝術(shù)。他嘗試新的生活方式與繪畫實驗,遠離京城他的單位和城中公寓。
而京城之東的宋莊畫家村,全然不是我初駐于它的情境:簡直成了一個藝術(shù)工廠;類似馬路超市的存在。道路變得夸張寬廣。高大的樓群居然聳立起來。畫廊林立。全然沒有過去的安靜小道與畫家隱在其中的院落畫室。藝術(shù)掮客在此出沒。各種以畫家為生的相關(guān)產(chǎn)業(yè)也隨之涌現(xiàn);偶見過去的熟悉的畫者普遍發(fā)富了,開著寶馬在馬路上駛過致使道路塵土飛揚。田野退縮,過去生長了近百年的白楊樹消逝不見;房地產(chǎn)商將視線轉(zhuǎn)入這里,和政府的視線一道,企圖將此打造成文化榜樣社區(qū)。
人們沒有想到畫畫的有這樣大的能量。政治資本警察介入此地。這是超出我的視界的陌異的宋莊。而高海軍在這個時刻以他個人身世和憶念置身于此。帶著他試圖變化改造自己繪畫的心愿。他不卷入于此,有限度地與少有幾個畫者串門走動,更多的時候在那有院子的花草間閑座;或轉(zhuǎn)身朝向高敞擺著梯子的空間,面對他的畫架默對或急促揮揮手臂,修改他的早年的畫面的布局或放棄他規(guī)避的陳舊觀念。
近三十年時間的差異和空間的遷變也呈現(xiàn)在他畫作的色塊和風物的表現(xiàn)中。早年畫作中的神性還在后期作品中的白塔和云影之間隱現(xiàn)。我們要做的不是對藝術(shù)的言說,而是要真正生活在其中。海軍的創(chuàng)作在三十年前抵達一個高峰,我愿他向另一個高處奔赴,重創(chuàng)他的繪畫高峰。他無法超越之前既成作品,他要另起爐灶,重建另一座峰巔。如果說,早期作品的色調(diào)是神廟的紫紅色,那么近期的作品則凸顯出都市的灰色調(diào)。
藝術(shù)作品生長于創(chuàng)作者的生活情境。北京時期的繪畫呈現(xiàn)都市情景,大街風物,地鐵和公交站點的色塊呈現(xiàn),都市的光影迷離。有如印象派畫家們晚期轉(zhuǎn)向都市。高海軍的后期作品讓我想到馬奈《旗幟飄揚的蒙尼埃街》。畫布的色塊變厚了,似乎掛在畫布上,凸顯畫作的立體褶皺;畫筆觸及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從早期繪畫的山嶺河流農(nóng)家的風物中脫離出來,現(xiàn)代都市諸元素在加強畫面的構(gòu)建,以其個人視覺來瞬間呈現(xiàn)與粘連組合不同的時空。另外,他的繪畫加入了跨文化的互動與轉(zhuǎn)化,呈現(xiàn)出不同于早期的人文氣象。在我看來,他后期的作品與前期的構(gòu)成微妙的互動,比如畫布都有云象,但氣象不同于以往。云變了不是早年畫布中純粹的云象了,那有著如德加舞女旋轉(zhuǎn)出來的樂感,從近作可以捕捉到他早年畫意的回聲。當然,后期的畫作與前期作品構(gòu)成了主題與技藝的完型構(gòu)成,如同他行走生命達成的某種圓滿感。

2006年柳宗宣在沈園,主持頒獎會
“我們都是德國浪漫派”
那幅有兩個葫蘆的油畫掛在一樓大門右側(cè)。下樓時,又看見了它,當寫作這段回憶性文字,重新進入我的凝視。那兩個形狀不一的葫蘆讓人耐看,它不借助外在光顯現(xiàn);它在自我發(fā)光,讓我看見它的表面和內(nèi)在空間以及他背后隱現(xiàn)的時空以及時空遷變中的人與事。
那個畫者不知到了哪里,聽說他離開了宋莊,后來到了上海。失聯(lián)了,不知他是否還在畫著。隔了這么久遠的光陰,他也不知我流落到了哪里。在宋莊他的曾經(jīng)的院落,某個黃昏和清晨,他乘興畫下兩只葫蘆。這些年,它脫離了消逝的宋莊那個時空那個院落,隨行在我不同的生活空間,抽象成了一件作品;與創(chuàng)作者分離,成為被我書寫的對象或生命。
某日。閑坐在山房旁大石頭上。忽然想到,在人類的世界,如哲人說的,應當把人當作目的而非手段;在藝術(shù)的世界,創(chuàng)作者應將文本當成目的,它本身就是自己的法則和目的。完成你的作品,這是最高的也是最后目的。我把這段話通過微信轉(zhuǎn)給身在北京的高海軍。
過去如身邊的收藏的書畫陪伴在我的身邊。早年,我向主編推薦他參與《青年文學》平面設(shè)計,喜歡經(jīng)過他制作設(shè)計的封面和內(nèi)文片式??膫€字讓我叫好。我是看著他在辦公室將青年文學幾個字用鉛筆勾勒在白紙上,掃描后通過coreldraw軟件在電腦調(diào)整、制作,然后出現(xiàn)在每期的刊物上,發(fā)送給全國的訂戶。作為刊物的編輯感受到榮光。那年刊物分成上下半月,他又重新制作設(shè)計,《青年文學》的設(shè)計創(chuàng)意是以英文特種字體與“青年文學”設(shè)計字體合成并置,構(gòu)成鮮明的風格。封面LOGO,極具符號識別性。整體設(shè)計中,以期號、顏色的變化形成各期的不同。

高海軍為柳宗宣主編的刊物設(shè)計的草圖
這些年,發(fā)現(xiàn)他參與了我的文學事業(yè)。我回到南方來后編輯的《藝文書》《新文學》《新詩學》,他都參與進來,是這些書刊的美術(shù)總監(jiān)。我主編的這些東西,他服務(wù)于它的封面內(nèi)文插圖版式,從我這里沒有得到任何報酬,完全是友情合作。他知道我是受著窮在從事個人的文學志業(yè)。有時打來電話,問詢我喜歡他的文章哪一個題目和片斷更合適些,他在這方面有些信任我,這些年,時光將我們演變成了彼此藝術(shù)共同體成員。某日。在漢口,翻閱我們共同編輯的書刊,頗有感慨。這是紀念在京十年的一種方式。女兒與妻子協(xié)助我自信自足地完成它。早年在京,三口之家就是一個微型出版工作室。在單位工作之余,參與其工作室的編務(wù),老高也偶爾參與進來,解決某本書稿的設(shè)計。有意思,多年前在北京經(jīng)營過的“八月之光藝術(shù)研究院”還在服務(wù)于我的語詞生涯,為之服務(wù)效力。原來,北上闖蕩鼓動家人辦公司是為了服務(wù)于個人寫作,這類似于朱湘的辦書店、戴望舒辦報館,皆是曲線救個人的寫作。我們的寫作是需要外力來養(yǎng)護的,我們所有的身份的扮演維護一些人看不上的隱在的志向:維持作為一個寫作者的存在。
2009年初夏,我離開北京從某地鐵站出來,望了望北京城,它空了,我沒有和高海軍道別,在三里屯那個十字路口我們從酒店出來有過提前的道別。在離開北京的傍晚,就想著找一個地方隱下來,幾年后,在大崎山間,我蓋了山房如多年前我所愿,他曾為山舍畫過幾幅油畫,從我的微信視頻中,他熟知了這里,他將它轉(zhuǎn)移到畫布上。然后,我將它插入新出的散文集《語詞地理》中,以此方式紀念我們之間的友誼,那是讓我們長久地在一起的可能的方式;也可以這樣表述,他的畫和我的語詞凝固了我們之間的友誼或曾經(jīng)在世的互動往來。
這些年來,我們在不同的時空地點談藝。我曾和他提及過詩人馬拉美的位于巴黎羅馬街八十七號住宅星期二沙龍。畫家馬奈、德加、作曲家德彪西是那里的???。藝術(shù)家們從對方的獲得藝術(shù)的滋養(yǎng)和啟發(fā)。我對他說過,馬奈以馬拉美為模特描繪油畫作品讓人叫好,前者畫出了后者的神韻;那是藝術(shù)家之前友情的象征和紀念。


高海軍為柳宗宣山舍而繪制
忽然發(fā)現(xiàn)這些年與海軍建立起游動的藝術(shù)沙龍,在歲月時光中的房子。酒店。辦公室。大巴汽車內(nèi)和私車駕駛室。畫室。行走的途中。他的畫喚醒了我;我的語詞助成了他的靈思。我們相互激發(fā),人文情懷在與彼此的交往中得到回應,產(chǎn)生回音?;蛘?,我們的交往在藝術(shù)的光照得到沐浴和提升。我的某句話于他似乎具有安慰性的撫摸效果;我們互為傾訴的對象交談的伙伴。我們曾經(jīng)在一起,朝向我們的自性奔走,如同他畫中的一群人朝向遠方的寺宇和云朵。
回憶讓我們重返抽象的神靈的光照中,如同他在繪畫獲得的超凡時刻,如同我在寫出好東西的神靈附體的凈身之感,我們不再是平常的卑瑣勢利的無趣的家伙,寫作與繪畫讓我們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藝術(shù)有著某種救贖功效,阻止精神下墜,朝向的多維存在。我們服務(wù)于詩歌和繪畫藝術(shù),我們都是德國浪漫派。是這樣的,這些年與海軍建立了游動的沙龍。我曾到他在北京的不同的房子,曾在他的地下車庫上樓,到達他的公寓,站在他的油畫作品前;酒后閑聊夜深,就睡在他的沙發(fā)上。某日,電話中催他從北京暫時離開,來到遼闊的南方的山野,到我的看云山房喝酒,像多年前到我的京東皇木廠四區(qū)六十三號的會飲。我說,背上你的畫架來吧,把我的工作室的大廳即興改造成你的畫室。
高海軍在電話中保持著他過去說話語音節(jié)奏。他說他還在畫畫,不是疫情,他說會即刻出行。重溫他贈給我的他在三聯(lián)出版的那本《步行者——一個畫者對時光的記錄》。扉頁上留有他簽名,贈書時間為2012年5月22日。我的目光落在扉頁他的照片:鴨舌幅。墨鏡。背景為起伏的山嶺。照片中他的目光投向遠山。照片下面的文字說明,他當時正在通往天祝草原途中,穿著我喜歡的雙腿兩側(cè)有荷包的褲子。真的,希望他能置身荒野即便人造的荒野,能重返寫生的遠途中。
(本文選自于《西湖》雜志2022年第十期)

>相關(guān)新聞
|
|
|
頂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線----------------------------
- 上一篇:天空之眼瞰登封“天地之中”歷史建筑群
- 下一篇:沒有了